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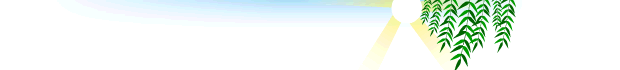 |
|
||
陈公博介绍 ┌───────┬───────┬───────┬───────┐ │ 命理咨询服务 紫微斗数简化命盘www.mlzxfw.com │ ├───────┬───────┬───────┬───────┤ │天机 │紫微权 │ │破军 │ │天钺天喜 │ │天月 │铃星 │ │孤辰天空 │天福凤阁蜚廉 │旬空 │天姚龙池 │ │飞廉 劫煞晦气│喜神 灾煞丧门│病符 天煞贯索│大耗 指背官符│ │64─73长生乙巳│74─83沐浴丙午│84─93冠带丁未│ 临官戊申│ │迁移宫 │疾厄宫 │财帛宫 身宫│子女宫 │ ├───────┼───────┴───────┼───────┤ │七杀 │ │ │ │台辅 │公历:1892年10月19日20时33分 │地劫 │ │天刑 │ │天厨 │ │奏书 华盖岁建│农历:壬辰年八月廿九戌时 │伏兵 咸池小耗│ │54─63养 甲辰│ │ 帝旺己酉│ │奴仆宫 │乾造:壬辰庚戌甲申甲戌 │夫妻宫 │ ├───────┤ ├───────┤ │太阳天梁禄 │起运:6年0个月 │廉贞天府 │ │天魁右弼 │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 │陀罗 │ │天才截空 │运:189819081918192819381948 │天官天虚 │ │将军 息神病符│ │官府 月煞大耗│ │44─53胎 癸卯│子年斗君:卯 │ 衰 庚戌│ │官禄宫 │ │兄弟宫 │ ├───────┼───────┬───────┼───────┤ │武曲忌天相 │天同巨门 │贪狼 │太阴 │ │文曲天马 │地空 │文昌擎羊火星封│禄存左辅科红鸾│ │月解天哭截空 │寡宿破碎 │阴煞 │天巫大耗天寿 │ │小耗 岁驿吊客│青龙 攀鞍天德│力士 将星白虎│博士 亡神龙德│ │34─43绝 壬寅│24─33墓 癸丑│14─23死 壬子│04─13病 辛亥│ │田宅宫 │福德宫 │父母宫 │命宫 │ └───────┴───────┴───────┴───────┘ 王亭之论:陈公博为抗日战争时期汪政权主要人物。汪精卫死后,谧任国府主席,旋即失败,被判汉奸罪枪毙。 笔者研究陈公博的命盘,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兄弟宫。 兄弟宫中廉贞天府化科,会紫微化权。结构甚佳,故得与汪精卫结为生死之交,且受提拔,惜同时会上武曲化忌与天相,而且见天马而不见禄存,见文曲而不见文昌。 凡六亲宫位见单星者,力量或不足,或有欠缺,最宜详细推断。现在陈公博的兄弟宫既见两颗单星而不见禄,又见武曲化忌,则于紫微化权、天府化科的好处之外。自然亦主受牵连拖累。 四十四至五十三岁的大限,兄弟宫在寅官,正是武曲化忌与天相同度的宫位,对宫的破军化禄冲起武曲化忌,铃星陀罗照会,所以汪精卫虽可在事业上对他加以扶持,官拜政权的行政院长,俨然元首的副贰,但事实上却是对他的连累。 一交五十四岁,走甲辰大限,兄弟官太阳化忌,擎羊入度。既然一路推查,其兄弟宫的曜都不吉,现在又见太阳化忌,自然可将其发展的脉络加以联系。是年为一九四五年乙酉,流年兄弟宫恰恰又为破军化权冲被陀罗挑起之刑忌夹印及丰陀夹忌的天相武曲化忌,再加上羊陀火钤冲照,则虽继汪精卫之后成为国府主席,其中之凶败固不待言矣。 兄弟宫一般用来查看兄弟与自己的关系,但亦可用来杏一看跟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如清代的同门同年,现代人的同志。汪精卫与陈公博在国民党中开系甚深,所以他跟陈公博的关系,应在陈氏命盘中的兄弟宫来追查推断。 附: 陈公博(1890年10月19日一1946年6月8日),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1890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1927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1928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革命评论》。1931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1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 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6月8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相关事件 第一面人生:中共一大代表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第二面人生:国民党大员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精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第三面人生: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 1946年6月3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童年陈公博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广州北门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红挂彩,鞭炮鸣爆,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一颗新生命在这天呱呱降临人间。年届60岁的广西提督陈志美因晚年得子而兴奋不已,为子起名“公博”。 陈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北部山区乳源。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举家迁居广州。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官至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禄,并保留官职称谓。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陈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独子的关系,自幼受到父亲的钟爱和放纵。因此,他幼年的学习生活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陈公博自6岁起便醉心于各种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文广平南平北》、《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去露天书场听“讲古”。那时,在广州禹山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设有好几个书场,由说书先生讲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旧小说。这种地方是社会上三教九流汇聚之处,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会被允许去的。但是,陈公博却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听说书。这种书场采用烧香的办法计时收费,每烧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纳5个铜钱,或1个铜板。说书先生为着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调,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长而又长,以吊众人的胃口。陈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亲买来小说自己读。很多字认不得,太繁难的便请教人,可以以意为之的便自己乱读。陈志美迷信开卷有益,认为小孩子不妨让他多知点东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镜和反省的机会。他不仅同意让陈公博随意阅读各种旧小说,而且还提些问题进行考问,诸如“《三国演义》内用两个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诸葛孔明在演义内骑过多少次马?”鼓励陈公博在阅读小说上用功;他甚至不理会陈公博阅读被列为坏小说的《金瓶梅》、《品花宝鉴》等禁书。陈公博成年后回忆说:“有时他瞥见我看小说,本来想问我看什么书,倘若他疑似我看坏书的话,就借故扬长地走开,装作不见。”“不过这是不是一个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益的。”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骚》,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发布者:
岑宵子
|